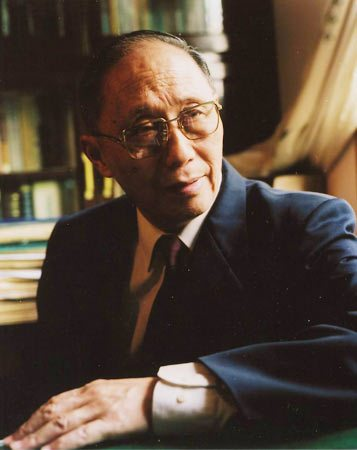 刘大宇. (来源:武汉大学官网) 刘道玉,1933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市。 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2年被聘为助理教授,1985年晋升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教务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第一高等教育办公室主任,还兼任中国化学会第22届、第23届理事会理事。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刘道玉作为会议秘书之一参加了邓小平主办的科学教育工程座谈会。 PairHe参加全国高校广告等重要会议任务评选活动大会和研究生院活动座谈会,为恢复高考与研究生教育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开创了教育和教育改革的新潮流,带头实施了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学生转学制、专业转学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下为刘道愚所著《教育改革论文集》序言。 《教育改革随笔集》作者:刘道宇编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会怀念,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才是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一般来说,我们受环境的影响很大我们成长于其中,接受过教育,读过经典名言。人是社会人,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就像演员扮演角色一样,必须扮演一个角色,有些是自己选择的,有些是安排的。无论是你自己选择的角色,还是被分配的角色,只要你用心、用心去演,就能把人生的一出戏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已经进入了“眉书”时代。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有两个人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是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工程师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一位是中国现代伟大作家鲁迅。在我30岁之前,诺贝尔奖影响了我的发展。 14岁时,他读了《发明王诺贝尔的故事》,并发誓将来要成为像诺贝尔一样的发明家。于是1953年,我参加了高考,考入了武汉大学。我进入了化学系,为了实现诺贝尔发明家的梦想,我考入了前苏联科学院,获得了化学副学士学位,专注于有机氟化学的研究。然而,在悲惨的文革十年里,“知道的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教书带来厄运”、“臭九岁老头”等口号,迷惑了人们的思想,混淆了善恶的界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未来陷入危机,而我成为诺贝尔奖级别的发明家的梦想似乎破灭了。 1976年秋天,灾难性的“革命”终于结束了,我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明家的梦想又复活了。然而,好景不长,历史再次给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被教育部借调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被任命为教育部委员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我很不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拒绝,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怠慢自己的职责,所以我被迫承担起拨乱反正的重担。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任务会改变我的生活。我也可以说它丰富了我的生活。 1979年3月,在完成了教育界的整顿使命后,我义无反顾地辞去了教育部的一切职务,回到了武汉大学。尽管最初想重操旧业,但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武汉大学行政副书记、常务副校长。一年多后,我被调任党委副书记、主席。从此,我开始了教育改革之路。我的梦想是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发明家不得不戛然而止,因为我失去了可以实现获得诺贝尔奖梦想的实验室。与其两头失败,我想还不如把重点放在顶尖学校上,把成为诺贝尔奖发明家的梦想变成实施教育改革的梦想。投入教育改革后,对我的思想、品格、信仰、气质、作风影响最大的人就是鲁迅先生。我很尊敬他,因为我年轻时读过他的很多散文和小说,深受他的思想影响。他在《空谈》和《论公平游戏的倒塌》的反面写道:“改革自然会涉及流血,但流血并不等同于改革。”“但我敢说,反改革派对改革派的恶毒从未放松过,他们的手段也变得更加强大。虽然我还在睡梦中,但吃亏的总是改革者,“中国永远不会有改革。”远离改革的艰难险阻,而是怀着“喜游虎山,知山有虎”的冒险精神,我决定成为武大教育改革的潮流引领者。不幸的是,我的结果被鲁迅先生预言了。1988年2月10日,我无故被免职。这是对我国大多数改革者命运的考验。我曾经想用标题“教育改革的呐喊”。我之所以决定用这个标题,显然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我读大学一年级时,读的第一本鲁迅小说是《呐喊》,这本书写于1918年至1922年间,出版前已出版了30多个版本,但我不记得是在哪家出版社读的。深刻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矛盾1911年革命到五四运动,残酷地揭露了食人的封建社会。本书从民主出发,以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希望唤醒人民的精神,启迪愚昧的人民,改变人民的陋习。我非常感谢鲁迅先生的呐喊精神。这是他的民主斗士和无条件精神的体现。他是一个无愧于中华民族“魂之子”的人。所谓喊叫,是指喊叫、恳求、提高声音、欢呼、呐喊、批评、批评等。一个人是否敢于喊叫,关键在于他是否无私、勇敢。他有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精神吗?卢先生批评道。在鲁我们也非常感谢“茹子牛”的付出。我在实施教育改革时,形容自己是一头勤劳的牛,总是耕荒耕耘,开拓新领域。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枚“先锋牛”徽章,我至今仍珍藏着。当我被解雇、失去改革阶段的教育时,我转身,变成杜鹃鸟,继续呼吁教育改革。我们深知个体的力量是弱小的,无法克服僵化的统一教育制度,但我们也不能只是坐以待毙。那时,我想起了啄木鸟,尝试去做一些能够创造优势、消除劣势的事情。基于这个想法我写了两本书:《教育问题探讨》和《论爱的教育》。我们希望这些信息对教师、学生和家长有用,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即使它影响到 10 或 100 人,那也是一件好事。幸运的是,这两本书自出版以来已经多次重印。前者荣获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后者被《尚书》一致评选为“2020年十佳图书”第一名ai Godo 出版社书店。这本藏书包括54篇手稿,它们是我三十年来倡导教育改革的忠实记录。教育评论、访谈、对话、提案等,都围绕着号召教育改革的主题。 《尖叫》作为主线贯穿每一章。其中,大部分稿件过去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而各种采访的内容大部分尚未发表。在写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写了十多篇新文章,其中大部分都受到了我的思想启发,再次体现了我孜孜不倦的学习、思考和写作的精神。宋代诗人王令在《过春记》中有两句:“子贵半夜仍哭血,不信东风不把他带回来。”我非常欣赏这两句台词,我哭泣的目的是为了找回埃德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教育改革。但改革充满风险,道路曲折,代价需要几代人的付出。也许改革可能会遭受一段时间的挫折,但我相信后人会沿着改革者的脚步继续前进,正如屈原在朱慈《礼牧》中所说:“路愈走愈远,上下求索。”一个虔诚的改革者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否则改革事业就不可能实现。泰康居楚园刘道玉 序/摘录:沉璐/编辑:何安南/校对:张晋/赵琳
刘大宇. (来源:武汉大学官网) 刘道玉,1933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市。 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2年被聘为助理教授,1985年晋升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教务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第一高等教育办公室主任,还兼任中国化学会第22届、第23届理事会理事。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刘道玉作为会议秘书之一参加了邓小平主办的科学教育工程座谈会。 PairHe参加全国高校广告等重要会议任务评选活动大会和研究生院活动座谈会,为恢复高考与研究生教育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开创了教育和教育改革的新潮流,带头实施了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学生转学制、专业转学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下为刘道愚所著《教育改革论文集》序言。 《教育改革随笔集》作者:刘道宇编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会怀念,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才是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一般来说,我们受环境的影响很大我们成长于其中,接受过教育,读过经典名言。人是社会人,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就像演员扮演角色一样,必须扮演一个角色,有些是自己选择的,有些是安排的。无论是你自己选择的角色,还是被分配的角色,只要你用心、用心去演,就能把人生的一出戏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已经进入了“眉书”时代。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有两个人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是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工程师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一位是中国现代伟大作家鲁迅。在我30岁之前,诺贝尔奖影响了我的发展。 14岁时,他读了《发明王诺贝尔的故事》,并发誓将来要成为像诺贝尔一样的发明家。于是1953年,我参加了高考,考入了武汉大学。我进入了化学系,为了实现诺贝尔发明家的梦想,我考入了前苏联科学院,获得了化学副学士学位,专注于有机氟化学的研究。然而,在悲惨的文革十年里,“知道的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教书带来厄运”、“臭九岁老头”等口号,迷惑了人们的思想,混淆了善恶的界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未来陷入危机,而我成为诺贝尔奖级别的发明家的梦想似乎破灭了。 1976年秋天,灾难性的“革命”终于结束了,我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明家的梦想又复活了。然而,好景不长,历史再次给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被教育部借调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被任命为教育部委员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我很不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拒绝,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怠慢自己的职责,所以我被迫承担起拨乱反正的重担。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任务会改变我的生活。我也可以说它丰富了我的生活。 1979年3月,在完成了教育界的整顿使命后,我义无反顾地辞去了教育部的一切职务,回到了武汉大学。尽管最初想重操旧业,但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武汉大学行政副书记、常务副校长。一年多后,我被调任党委副书记、主席。从此,我开始了教育改革之路。我的梦想是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发明家不得不戛然而止,因为我失去了可以实现获得诺贝尔奖梦想的实验室。与其两头失败,我想还不如把重点放在顶尖学校上,把成为诺贝尔奖发明家的梦想变成实施教育改革的梦想。投入教育改革后,对我的思想、品格、信仰、气质、作风影响最大的人就是鲁迅先生。我很尊敬他,因为我年轻时读过他的很多散文和小说,深受他的思想影响。他在《空谈》和《论公平游戏的倒塌》的反面写道:“改革自然会涉及流血,但流血并不等同于改革。”“但我敢说,反改革派对改革派的恶毒从未放松过,他们的手段也变得更加强大。虽然我还在睡梦中,但吃亏的总是改革者,“中国永远不会有改革。”远离改革的艰难险阻,而是怀着“喜游虎山,知山有虎”的冒险精神,我决定成为武大教育改革的潮流引领者。不幸的是,我的结果被鲁迅先生预言了。1988年2月10日,我无故被免职。这是对我国大多数改革者命运的考验。我曾经想用标题“教育改革的呐喊”。我之所以决定用这个标题,显然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我读大学一年级时,读的第一本鲁迅小说是《呐喊》,这本书写于1918年至1922年间,出版前已出版了30多个版本,但我不记得是在哪家出版社读的。深刻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矛盾1911年革命到五四运动,残酷地揭露了食人的封建社会。本书从民主出发,以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希望唤醒人民的精神,启迪愚昧的人民,改变人民的陋习。我非常感谢鲁迅先生的呐喊精神。这是他的民主斗士和无条件精神的体现。他是一个无愧于中华民族“魂之子”的人。所谓喊叫,是指喊叫、恳求、提高声音、欢呼、呐喊、批评、批评等。一个人是否敢于喊叫,关键在于他是否无私、勇敢。他有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精神吗?卢先生批评道。在鲁我们也非常感谢“茹子牛”的付出。我在实施教育改革时,形容自己是一头勤劳的牛,总是耕荒耕耘,开拓新领域。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枚“先锋牛”徽章,我至今仍珍藏着。当我被解雇、失去改革阶段的教育时,我转身,变成杜鹃鸟,继续呼吁教育改革。我们深知个体的力量是弱小的,无法克服僵化的统一教育制度,但我们也不能只是坐以待毙。那时,我想起了啄木鸟,尝试去做一些能够创造优势、消除劣势的事情。基于这个想法我写了两本书:《教育问题探讨》和《论爱的教育》。我们希望这些信息对教师、学生和家长有用,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即使它影响到 10 或 100 人,那也是一件好事。幸运的是,这两本书自出版以来已经多次重印。前者荣获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后者被《尚书》一致评选为“2020年十佳图书”第一名ai Godo 出版社书店。这本藏书包括54篇手稿,它们是我三十年来倡导教育改革的忠实记录。教育评论、访谈、对话、提案等,都围绕着号召教育改革的主题。 《尖叫》作为主线贯穿每一章。其中,大部分稿件过去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而各种采访的内容大部分尚未发表。在写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写了十多篇新文章,其中大部分都受到了我的思想启发,再次体现了我孜孜不倦的学习、思考和写作的精神。宋代诗人王令在《过春记》中有两句:“子贵半夜仍哭血,不信东风不把他带回来。”我非常欣赏这两句台词,我哭泣的目的是为了找回埃德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教育改革。但改革充满风险,道路曲折,代价需要几代人的付出。也许改革可能会遭受一段时间的挫折,但我相信后人会沿着改革者的脚步继续前进,正如屈原在朱慈《礼牧》中所说:“路愈走愈远,上下求索。”一个虔诚的改革者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否则改革事业就不可能实现。泰康居楚园刘道玉 序/摘录:沉璐/编辑:何安南/校对:张晋/赵琳